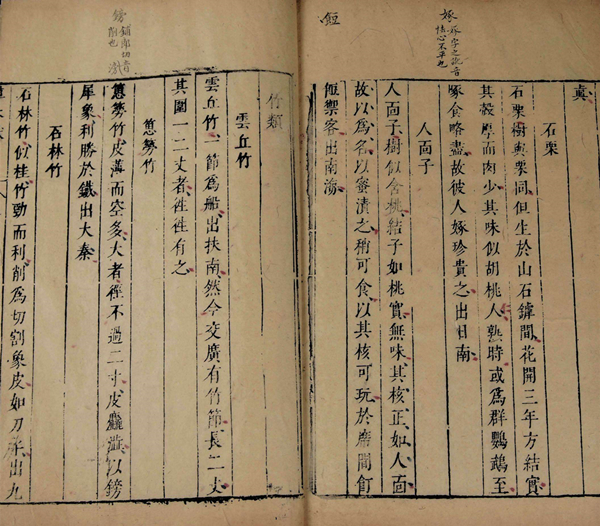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1170个作品,作者:乔乔,配图:作者提供、网络图片
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谈论性别问题是相对敏感的。而跨性别者作为性少数的少数,其处境之艰难便更少为人知。
对于跨性别女性来说,男儿身,女儿心,这种的割裂感是一种隐秘的、不足与外人道的痛苦。有些人会选择通过服用或注射药物等手段,使自己的生理状态更接近真正的女性。这类人有一个特别的称呼:药娘。
刚接触药娘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些跨性别者要选择私下进行服药,而非正规就诊或接受手术?但在深入聊天和了解之后,我认识到了她们选择的必然性。亲密关系的断裂、医疗体制的缺失以及大众认知的污名化等现实问题,都是横亘在这个群体眼前、不得不直面的一座座高山。
当身体背叛灵魂,药娘们的人生又将何去何从?
1、“如果我能成为一个女孩”
阿诚最近发现,自己总是会在厕所吓到人。
大约两周前,阿诚刚要踏出厕所,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瞥见阿诚,男人惊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美女抱歉!”阿诚正想解释,那人随即拐进另一侧的女厕所。两三秒后,隔壁传来一声女性尖叫。中年男人重又踉踉跄跄返回来,眼睛直勾勾盯着阿诚,皱眉问:“你是男的?”阿诚轻轻点了下头,避开男人惊异的目光,头也不回快步离开。
阿诚是一名药娘,依靠服用激素类药物,改变自己作为男性的原生性别。毫无疑问,她拥有着一切男性生理体征,但在性别认知层面却是完完全全的女性。
作为一个跨性别女性,二十多年以来,这种不间断的分裂感,时刻笼罩在她生活的方方面面。
太阳落山,一轮隐隐的月牙挂上夜空。阿诚面对着一衣柜的琳琅满目,左挑右拣,最终还是选定那件最爱的粉色长裙。细细地整理好假发,阿诚望着镜中娇俏的脸庞出了神。
一个裙摆飘飘的甜美女孩,那是她的另一副面孔。
女性的灵魂被拘束在男性的躯干之中,身体便是阿诚最大的敌人。

跨性别者的定义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代指性别认同和表达异于其天生指派性别的人。其中,跨性别女性表现为以男性的性别出生,却拥有女性的性别认同。跨性别者的觉醒,通常随着自我认知的成熟,表现为一个持续且渐进的过程。
2015年,十八岁的阿诚走入大学校门。父母离婚多年,阿诚从小被母亲抚养长大,大学之前,她的男性朋友掰着一只手都能数过来。
那时的阿诚,对自身性别认知还只是懵懵懂懂,但察觉到了自己与舍友们的格格不入。
最让她头疼的便是洗澡问题。寝室内自带一个狭小的冲凉间。舍友们总是要在外面先脱光再进浴室。日子长了,舍友们都嘻嘻哈哈习以为常,而阿诚始终无法忍受裸露的男性胴体频繁在寝室内走动。她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却换来了一通嘲笑:“你小子怕不是个女人吧?”
这句无心之言戳中了阿诚的隐痛,成为了她开始确认性别认同的契机。
大一暑假,阿诚确定了自己是一名跨性别女性。从幼年起积攒的性别迷惑,在十九岁那年终于得到了答案。
小时候,理发店对阿诚来说便是监狱一般的存在。每次母亲要带她去理发,二人便会大吵一场。尽管渴望着一头飘飘长发,但阿诚总是在逼迫下,不得已被剃成寸头。直到高中,母亲才终于妥协。但阿诚心里明白,自己想争取的不只是留长头发的权利。
在确认自己真正的性别后,她在日记中写道:“就算拿我全部的生命去换短短三天,我也想要作为一个女孩而活。”
2、此之砒霜,彼之蜜糖
大二开学前后,阿诚了解到药娘这个群体,但她真正决定成为一名药娘,则要更晚一些。
通俗来说,药娘就是通过吃“糖”来改变自身的一群跨性别女性。“糖”在药娘圈子里有着特殊的含义,不是普通的糖果,而是代指能够改变人体内分泌的激素类药物,通常分为抗雄激素、雌激素以及孕激素三大类。药娘们的内分泌便在吃“糖”中悄然改变。
阿诚挺喜欢这个代号:说的次数多了,生活仿佛就没那么苦了。
阿诚在QQ上加入了几个药娘内部交流群。药娘之间以姐妹互称,并时常在群里分享交流自己的故事以及吃药的心得体会,大家的故事基本大同小异:对自身性别产生怀疑,搜寻相关信息,继而采取行动改变。
一粒补佳乐、两粒黄体酮以及五十毫升色普龙,这是交流群里公开传授的药方。照此服用,每个月的花销大致在三百块上下。
由于母亲始终奉行着“穷养儿”的观念,阿诚在生活费上相当拮据。为了能够负担起药,她对每一餐都精打细算:一盒泡面或者一碗白粥,就能简单地应付一顿。阿诚甚至一直保持着一日只吃两餐的习惯,为的就是把每天花销控制在二十块以下。
除了吃“糖”外,注射针剂也是药娘们改变激素分泌的途径之一。针剂的产地各异,对应的价格也不一。一般来说印度、泰国的比较便宜,而日本、欧美产则要昂贵许多,但药效也更突出。好的针剂仅注射两三个月,胸部便能隆起一座小丘。
通常来说,一盒五到十支的针剂,价格在四百元到一千元不等,高昂的价格令诸多药娘望而却步。
阿诚从没想过注射针剂。一方面是价格,另一方面是担心不当注射引发不良后果。为了保护隐私,药娘们通常选择自主注射,而绝大多数人缺乏注射技术和经验。一旦注射不当,便会导致创口感染、肌肉萎缩等一系列严重后果。但即使如此,针剂的奇效依旧吸引着一大批药娘。
有交易的地方就有人性的挣扎。阿诚曾听闻,一些年龄小的药娘,由于瞒着父母,又没有经济收入,便选择通过援交的方式换取药品费用。
药娘所服用的激素类药物,通常是处方药。由于拿不到医嘱,阿诚在其他药娘的介绍下,选择从一些私售药品的药商处购买。在药商的淘宝店铺中,商品销售页面并不明确标注是药品,而是以配以服装、零食等不相符的图文描述。药娘通过QQ群等内部渠道,或直接在淘宝上搜索隐晦的关键词,和药商沟通后即可拍下商品。
大多数药商不具备从业资格证明,其所提供的药品质量很难获得保证。低级仿制的药品从外包装上便可以分辨,药品质量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药片易碎,且质地不纯、肉眼可见杂质。而对于高仿或是真假混卖的药品,药娘们只能以身试药,通过药效进行区分。
一旦确定某药商确系贩卖假药,药娘们便会在群体内部进行扩散。尽管如此,由于私下购买处方药违反法律规定,加之缺少交易凭证和相关法律知识,药娘们只得将苦水往肚子里咽。
交流群里时常有人晒出自己吃药前后的对比照片,并配以粉色泡泡的对话框:“吃‘糖’一百天,看看有什么变化?”
吃“糖”快两年,阿诚越发兴奋,因为自己看起来越来越像个女孩子了。皮肤摸起来又滑又腻,脸上的痘痘也去了大半。圆润的小脸配上大大的眼睛,加上悄然隆起的胸脯,和留长至肩的头发,路人基本辨别不出她的真实性别。
“可我现在的体力已经快废了。”阿诚有些黯然。
服用激素类药物,容易对身体造成极大的负担和伤害,阿诚之前就听说过,这也是她最初犹豫是否要吃“糖”的原因之一。刚开始时,她只是胸部隐隐作痛,以及时不时地眩晕一阵,吃了大半年后,嗜睡、体能下降以及睾丸疼痛等症状开始逐渐出现。交流群里一些吃得过猛的药娘,更是检测出了肝功能障碍。
阿诚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出门步行超过一个小时,即便是到隔壁小区的菜鸟驿站取快递,路程不过半她便气喘吁吁。上个月出去玩,尽管北风呼呼刮着,豆大的汗水却一滴一滴从阿诚的脸颊滑落,身旁路人时不时惊奇地瞥过来,让她很是尴尬。
真正成为一名药娘快两年,身体一天天地虚弱,但阿诚从未停止吃“糖”。她已经吃不出药的苦味,渐渐觉得“糖”就是甜的。阿诚说,她不指望旁人的理解和包容,“我只恳求不要攻击我,不要伤害我。”

与阿诚的聊天:“我就没想过能活很久”
3、“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呢?”
按照国内正规治疗流程,跨性别者需经专业医生诊断,获得易性症证明后,继而进行激素替代疗法。
然而阿诚表示,能够成功拿到易性症证明并不容易。
国内具有诊断资格的机构极为稀缺。而且,国内关于易性症的诊断是一个漫长而细致的过程。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为例,患者需在首次就诊后,至少随诊两年,期间至少3次就诊,间隔时间不短于1个月,才能明确给予判断。
供不应求下,药娘们想要获得名医看诊难上加难。
因为家乡没有专业机构,药娘媛媛曾专门到上海求诊。早上八点去挂号时,前面就已排了九十多人。太阳渐渐西沉,快到医生下班时,媛媛仍然没有得到面诊。她忍不住向助理护士抱怨:“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呢?”
小天也有类似的经历。由于不熟悉医生的出诊安排,她头一天先是跑空,第二天去取号时却被告知号已取完,下次医生坐诊要到五天后。这次一无所获的旅程,小天在住宿和交通花费了两千多元,等于半年的吃“糖”钱。
在易性症的诊断方面,目前学界仍存在争议。
从多数药娘提供的经历来看,国内精神科医生普遍认为,若跨性别者存在其他精神心理障碍症状,则优先诊断其他精神疾病。唯有认知、情绪状态都非常良好的情况,方可考虑诊断易性症。
然而,大量研究显示,易性症患者由于自身性别认同的显著不同,多伴有程度不一的情绪障碍。阿诚指出,网上有一些专门的药娘QQ群,会针对如何应对医生的面诊进行讨论,以此规避心理测查。
即便好不容易获得了证明,在激素替代治疗方面,国内针对跨性别者治疗的专业机构,仅有北医三院的“易性症治疗序列”一家拥有开具激素处方的资格,并为激素替代疗法提供指导意见。目前国内性别重置手术资源尚处于稀缺状态。起步时间晚,加之多数医院的开展积极性不高,能够满足规定的医疗机构与医生寥寥无几。
基于技术成熟度的考虑,药娘小马选择赴泰国完成性别置换手术。去年,小马偶然在QQ群看到一个账号发布信息,其自称是从事泰国手术代理的中介,全程代办一切手术事宜。
那时小马已经自主服药快3年了,实施手术的想法在她心中日渐成熟。与家人和朋友商议后,小马最终选择通过这家中介联系手术。中介提出收取1000元的服务费,并承诺全程翻译和定期看护服务。
母亲提出要陪护小马,但小马考虑到母亲年岁已高,不想让她看到自己手术后虚弱和血淋淋的一面而担心难受,便在向公司申请停薪留职两个月后,独自一人随中介赴泰进行手术。
国内的《性别重置规范》规定,手术前手术对象应当满足以下条件:对性别重置的要求至少持续5年以上,且无反复过程;以及术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疗1年以上且无效。
小马觉得相比于国内,赴泰手术的优点之一便是省时省力。手术前一个月,中介要求小马提交了一份HIV检测结果。到达泰国后,小马被中介带去一名心理医生处,开具了一份精神证明,整个过程不超过半小时。而这便是手术前所要准备的一切材料。
小马选择仅对下体实施手术,加上住院和交通等,花销共计约八万元。小马已工作多年,仍觉得这笔手术费有些昂贵,可又不得不做。
而对于大学刚毕业、至今仍待业在家的阿诚,动辄数万的手术费用不菲,她打算等工作几年攒够钱,再进行手术。
对于普遍年龄较低,尚未经济独立的药娘们来说,去正规医院进行手术是一笔巨款。部分药娘选择去无经营资质的诊所完成手术,但安全性却无法得到保障。
去年,阿诚的朋友小月终于说服家人,决定进行手术。小月十分高兴,却又有些难过,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自己终于可以享有别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了。
阿诚则还在苦苦煎熬着:“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呢?”
4、“我怎么就有你这样的儿子?”
医疗系统的稀缺,促使着一部分药娘持续私自用药。而亲人的态度,更是横跨在药娘获得正规治疗间的鸿沟。
按照规定,性别重置手术前,患者必须要提交直系亲属理解并同意性别重置手术的父母知情声明并进行公证。这意味着,性别置换手术的实施,需要征得父母的完全认同。
21岁的阿诚曾有一个梦想:在母亲接受自己的前提下,进行性别置换手术,变成真正的女孩。现在她23岁了,却对自己当初的想法嗤之以鼻。
“我把那个希望无限地放大,最后它就像泡泡一样,噗地一下破掉了。”

阿诚的桌子
2019年六月份,阿诚大学毕业,暂住西安的舅舅处静心准备考研。舅舅经营的诊所门店空着一间小起居室,阿诚平日便居住在此。
一次和舅舅外出途中,阿诚晕车严重,学医出身的舅舅替她号脉,发现阿诚的心脏出现问题。阿诚以自己失眠为由,随意搪塞了过去。本以为已蒙混过关,没想到几天后回到诊所的房间,她看到自己原本整齐摆放的药瓶,七七八八散落在打开的抽屉里。
阿诚知道到了该向母亲坦白的时候。趁着周末,她乘大巴回到了咸阳的家。她和母亲坐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聊着天。谈起小时候装修房间的事,阿诚开玩笑说:“怎么当时没给我装个公主床?”
母亲的神色变了。她瞪大眼睛,抓住阿城的肩膀:“你舅舅都和我说了。你是不是就一门心思想当个女生?”
阿诚头一次觉得母亲这么令她害怕。
自此之后,母亲的态度一直是淡淡的。有一次阿诚涂了指甲,母亲只是瞥了一眼,并没有开口指责。阿诚想,母亲是不是已经接受了事实,她也因此萌生出一丝希望。直到一次,二人因为一点小事吵架。母亲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拎起手边的抱枕摔在阿诚身上,冲着她吼:“你怎么就这么想做个女人!我怎么就有你这样的儿子?”
阿诚闻言默默回到房间,收拾好行李坐上了返程的大巴。
她想,母亲应该早就对自己的“异常”隐约有察觉了,只是不愿直面答案。“我妈一直把这个事记在心里,等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全部喷发出来了。我不想再说服她了,大家相安无事,这样最好了吧。”
但是,相比于药娘薇薇安来说,阿诚还是显然幸运许多。在向家人宣布自己的性别认同后,薇薇安被父亲用绳索捆绑起来,没收了手机以及身份证,并试图强迫她入住精神病院。薇薇安进行了激烈的反击,不慎从三楼坠落,腰椎骨折。在住院期间,父母仍不停指责她,并在伤愈后限制其出行。
《跨性别报告》显示,近九成的原生家庭不能完全接受跨性别孩子,尤其是有改变身体意愿或行为的跨性别者,其中最不能接受的,是跨性别女性。在来自原生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压力下,加之服用激素类药物导致的情绪波动,药娘们极易受到严重心理创伤。61.5%的人存在抑郁,73.2%存在焦虑,46.2%的人因为自己是跨性别而有过自杀想法,12.7%的人曾有过自杀行为。
阿诚很少出门,一个人住,也没有什么朋友,有时候一星期说的话两只手可以数过来。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她会躲在被子里默默流泪,哭累了就睡过去。
5、黑暗角落里的病人
在泰国顺利接受完手术,小马住院两周后,选择回家继续休养。两个月后,小马就已经恢复了行动,便向公司申请重新上班。
沉浸在喜悦中的小马没想到,就在手术结束10个月后,自己将要成为国内第一起跨性别平等就业权案的当事人。
小马就职于杭州一家文化传媒类公司,负责艺人助理以及拍摄仓库管理的工作。刚回到工作岗位,她就接到了人事部的约谈。人事部称她的状况已不适合继续工作,劝其主动提交辞职报告。
“你现在手术完以后,已经不适合再跟着艺人了。男艺人不方便,女艺人更是不行。”小马在某次约谈中,录下了对方的这段话。
春节假期接踵而来,小马发现应得的年终奖并没有到账。新年上班的第一天,经理笑着一路将开门红包发过来,却唯独跳过了她。小马僵在工位上,周围的同事不时瞥来一眼。此时小马心中,已隐隐地有所预感。2019年2月12日,小马查收到来自公司人事部的邮件:因为她考勤不合格,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2019年8月,小马以“平等就业权纠纷”为由,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方表示,小马确实存在考勤不合格的事实,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定理由,并否认了对小马存在歧视。小马则指出,公司氛围一直相对宽松,迟到早退现象在其他员工中常有发生,而公司也一贯持默许态度。她在法庭上要求提供其他员工的打卡记录,却遭到了公司的拒绝。
目前这起案件还在审理中。除了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外,小马还有着其他的诉求:她希望能够借由自己的案子,使得社会上更多的人能关注到这个群体,减轻跨性别者面临的不公。
大学毕业后,阿诚也面临着难题。学历证书上对于性别修改的限制,成为她犹豫是否接受手术的因素之一。由于缺乏明确相关规定,能否成功申请修改证书上的性别,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随机的校方态度。
不仅是就业和工作环境,跨性别者所遭受的歧视从学生时代就已初露端倪。《跨性别报告》显示,七成左右的跨性别者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校园暴力,其中跨性别女性占比最高。因为被男生们嫌“娘”,阿诚也经历过一段不愿回首的校园黑暗往事。
阿诚觉得药娘们的感受,旁人是无法真正体会的:“人生处处是围城,药娘们像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注定要过上比他人要严峻百倍的日子。”
2014年,拥有十万余关注数的“药娘吧”消失在大众视野里,随后建立的“药娘二区”、“药娘三区”等贴吧在数月后步其后尘。现在药娘间的交流大多借助QQ群,但也不时会遭到封禁。
对此,阿诚倒不觉得惊讶。部分药娘在贴吧里发布色情图片,吸引感兴趣的人进行援交;一些人拒绝承认激素对人体的影响,发布帖子宣传大剂量的用药方法;十四五岁的低龄药娘互相鼓励,瞒着家长随意吃药……这些都是贴吧中常见的帖子类型。
“丧”是药娘圈的主基调。药娘们热衷讨论的主题,离不开对社会、工作以及家庭等全方位的抱怨。
但阿诚觉得,这种风气不可避免。吃药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加之整个社会的歧视,药娘们的处境本就不乐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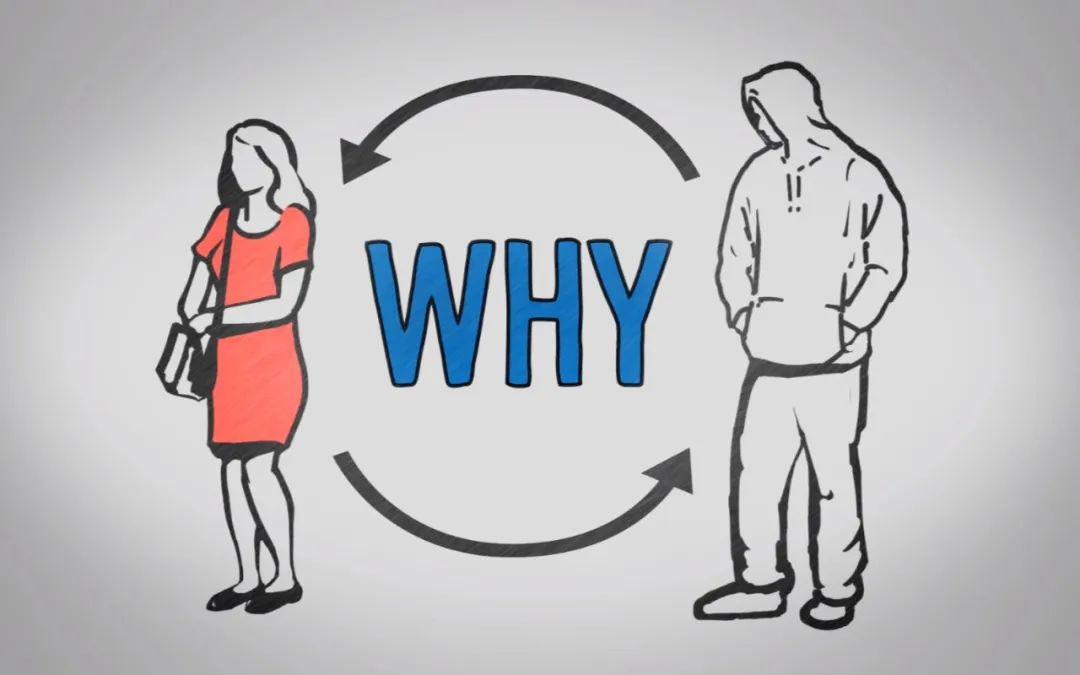
2019年5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在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第 11 次修订,将“性别认同障碍”从精神障碍的分类中移除,更名为“性别不一致”,并重新归入“性健康”一栏。但在国内,性别认同障碍仍被视作是精神疾病的一种。
一次特殊的交友经历,让阿诚至今印象深刻。在某节英语课上,阿诚因为共看一本书与女孩豆豆熟悉起来。她鼓起勇气,加了豆豆的微信,但很快阿诚就发现,自己被豆豆屏蔽了。
后来豆豆解释,自己一开始只是觉得阿诚性格孤僻,但在翻阅了她的朋友圈,继而在网上搜索到药娘的含义后,她害怕了。
阿诚仍清晰地记得豆豆的一句话:“对不起,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药娘,我觉得很恐怖。”
“我们在他人眼中,仍然是黑暗角落的病人。”阿诚说。
她有时候觉得自己还不如得了癌症,起码有正规渠道可以治疗,父母也会关心体恤,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人当作怪物。
阿诚打算考研到南方的临海城市,听说那里山好水好人也好。但随着身体和精神一天天地坏下去,阿诚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到那一天。每天的“糖”还在继续吃,但她无所畏惧。
“我不在乎还能活多久。”她说,“反正不剩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注:文中使用姓名均为化名)